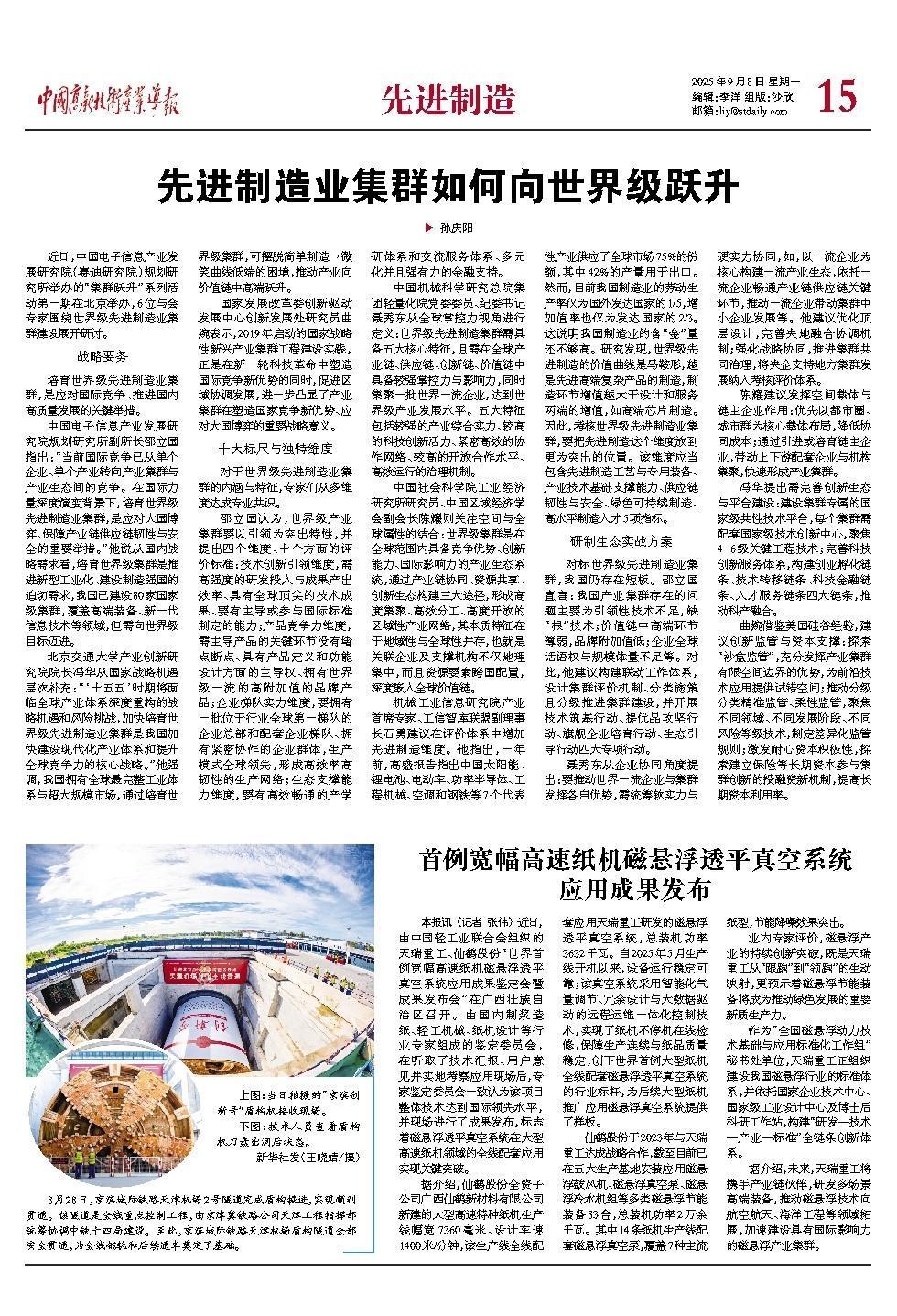▶ 孙庆阳
近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规划研究所举办的“集群跃升”系列活动第一期在北京举办,6位与会专家围绕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展开研讨。
战略要务
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应对国际竞争、推进国内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邵立国指出:“当前国际竞争已从单个企业、单个产业转向产业集群与产业生态间的竞争。在国际力量深度演变背景下,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应对大国博弈、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重要举措。”他说从国内战略需求看,培育世界级集群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的迫切需求,我国已建设80家国家级集群,覆盖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但需向世界级目标迈进。
北京交通大学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冯华从国家战略机遇层次补充:“‘十五五’时期将面临全球产业体系深度重构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加快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我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战略。”他强调,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与超大规模市场,通过培育世界级集群,可摆脱简单制造→微笑曲线低端的困境,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创新发展处研究员曲婉表示,2019年启动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工程建设实践,正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同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凸显了产业集群在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应对大国博弈的重要战略意义。
十大标尺与独特维度
对于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内涵与特征,专家们从多维度达成专业共识。
邵立国认为,世界级产业集群要以引领为突出特性,并提出四个维度、十个方面的评价标准:技术创新引领维度,需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与成果产出效率、具有全球顶尖的技术成果、要有主导或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能力;产品竞争力维度,需主导产品的关键环节没有堵点断点、具有产品定义和功能设计方面的主导权、拥有世界级一流的高附加值的品牌产品;企业梯队实力维度,要拥有一批位于行业全球第一梯队的企业总部和配套企业梯队、拥有紧密协作的企业群体,生产模式全球领先,形成高效率高韧性的生产网络;生态支撑能力维度,要有高效畅通的产学研体系和交流服务体系、多元化并且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轻量化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聂秀东从全球掌控力视角进行定义: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需具备五大核心特征,且需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中具备较强掌控力与影响力,同时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企业,达到世界级产业发展水平。五大特征包括较强的产业综合实力、较高的科技创新活力、紧密高效的协作网络、较高的开放合作水平、高效运行的治理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则关注空间与全球属性的结合:世界级集群是在全球范围内具备竞争优势、创新能力、国际影响力的产业生态系统,通过产业链协同、资源共享、创新生态构建三大途径,形成高度集聚、高效分工、高度开放的区域性产业网络,其本质特征在于地域性与全球性并存,也就是关联企业及支撑机构不仅地理集中,而且资源要素跨国配置,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产业首席专家、工信智库联盟副理事长石勇建议在评价体系中增加先进制造维度。他指出,一年前,高盛报告指出中国太阳能、锂电池、电动车、功率半导体、工程机械、空调和钢铁等7个代表性产业供应了全球市场75%的份额,其中42%的产量用于出口。然而,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国外发达国家的1/5,增加值率也仅为发达国家的2/3。这说明我国制造业的含“金”量还不够高。研究发现,世界级先进制造的价值曲线是马鞍形,越是先进高端复杂产品的制造,制造环节增值越大于设计和服务两端的增值,如高端芯片制造。因此,考核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把先进制造这个维度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该维度应当包含先进制造工艺与专用装备、产业技术基础支撑能力、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绿色可持续制造、高水平制造人才5项指标。
研制生态实战方案
对标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我国仍存在短板。邵立国直言:我国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主要为引领性技术不足,缺“根”技术;价值链中高端环节薄弱,品牌附加值低;企业全球话语权与规模体量不足等。对此,他建议构建联动工作体系,设计集群评价机制、分类施策且分级推进集群建设,并开展技术筑基行动、提优品攻坚行动、旗舰企业培育行动、生态引导行动四大专项行动。
聂秀东从企业协同角度提出:要推动世界一流企业与集群发挥各自优势,需统筹软实力与硬实力协同,如,以一流企业为核心构建一流产业生态,依托一流企业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推动一流企业带动集群中小企业发展等。他建议优化顶层设计,完善央地融合协调机制;强化战略协同,推进集群共同治理,将央企支持地方集群发展纳入考核评价体系。
陈耀建议发挥空间载体与链主企业作用:优先以都市圈、城市群为核心载体布局,降低协同成本;通过引进或培育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与机构集聚,快速形成产业集群。
冯华提出需完善创新生态与平台建设:建设集群专属的国家级共性技术平台,每个集群需配套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聚焦4-6级关键工程技术;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构建创业孵化链条、技术转移链条、科技金融链条、人才服务链条四大链条,推动科产融合。
曲婉借鉴美国硅谷经验,建议创新监管与资本支撑:探索“沙盒监管”,充分发挥产业集群有限空间边界的优势,为前沿技术应用提供试错空间;推动分级分类精准监管、柔性监管,聚焦不同领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风险等级技术,制定差异化监管规则;激发耐心资本积极性,探索建立保险等长期资本参与集群创新的投融资新机制,提高长期资本利用率。